满山秋色,几袭秋凉
·彭晓玲
秋意正深,穿行于大围山的山山岭岭,我的视线掠过五彩斑斓的秋林。阵阵秋风袭来,挟着秋之醇香秋之微凉,乃沉醉不知归路。
何处祷泉湖
很久以前,就在大围山之巅,绵延着大片大片的高山草原,草原上散布着白沙湖、祷泉湖等大大小小的湖。且不说,此情此景颇有诗情画意,这些湖竟是浏阳河之源,更是令人振奋。
曾多少次,明媚的春日里,我奔赴大围山。还在山下,就想象着自己行于山顶湖畔,碧水微澜,水的清香草的清香团团涌来,草丛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小花。然后,我缓缓蹲在湖边,轻轻地撩拨清冽的湖水。但多少次,还在半路上,就无功而返,毕竟少有人愿意陪我去找寻藏于草原深处的湖。即使有人愿意陪我,可一到山顶,就失却了方向感,胡乱地转来转去,却总也找不到。便有淡淡的怅然。但我依然满怀期待,与祷泉湖美丽的邂逅。
就在前年春天,杜鹃花开满了大围山,我与友人爬到了山顶。但见山山岭岭,草色正嫩,树叶正绿,遍地的杜鹃花或纵情盛开,或含苞欲放。在花丛里流连,乃不知今夕是何夕。也许杜鹃花不如莲花清气,不如牡丹花贵气,但它红得纯粹,红得率性,也红得野气。大俗何尝不是大雅?每每看过杜鹃花,我便会联想到乡村那些大妈大嫂巧手剪出的大红窗花,红艳艳地贴在新年的玻璃窗上,喜气洋洋。
看得久了,猛然想起祷泉湖,便赶紧呼唤友人再往山顶上走。这次可有人带路,下了坡,沿长长的坡路转到另一山头上,再往前行。路更难走了,应是由雨水冲涮而成,好在路旁只是些草地,抑或不高的灌木丛,好在满眼都是纯静的绿色。实在累了,抬头看看,山脊还在往前往高绵延,野性十足。有人在远远的山顶上大嚷。可湖到底藏在哪里?
向导站在前方,回身朝我们招了招手,快来,祷泉湖到了!原本累得东倒西歪的我,振作起来了,急急奔上前去。没有看到满湖春水,却惊愕地看见了大片大片的芳草地。草地就山脊往下走不远处,绿意盎然,一条小溪流自草地穿过,散落着几块或大或小的水洼。听不到哗哗的水声,浓郁的水汽却弥漫而来。难道昔日盈盈湖水,穿越密密的年华,竟然演变成了湿地?难道深深浅浅的湖水就隐藏在重重青草之下?难道这真是浏阳河之源,最重要的源头?我正想顺着那条若有若无的小路,奔赴祷泉湖!向导却扯住了我,怎么能下去呢?谁也不知那些芳草地之下,到底有没有泉水,泉水有多么深?再看看那芳草地,似有无穷的神秘,随着水汽幽幽而来,缠绕着我笼罩着我。可望却不可即,我呆呆地站立在山脊上,任湿润的春风呼呼吹来。
只得怏怏而归。可多少日子逝去,日里梦里,祷泉湖的芳草地,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。我想,我得找机会再去看看。于是,在这深秋季节,我又奔赴祷泉湖而来。上得山来,白茫茫的雾竟遮天盖地。越往上雾越浓郁,四周景色倒清晰可见。驱车直往七星峰方向,直奔远远的山顶。将车窗略微摇下,将音响调大,任清凉的风吹进车内,任激越的鼓点响彻周遭。好似行于茫茫的荒山上,既不所来也不知所往,只有眼前这方秋色。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终是到了祷泉湖方向,便弃车登山。伴随茫茫的浓雾,我们踏上质朴的木质游道,应是刚刚整修而成。杜鹃树已落了不少叶子,瘦瘦地挤在一起,一派天真。之前来时,并没有游道直通祷泉湖,自浓雾里钻出来的修路人,却明确地告诉我们,游道便通往祷泉湖。四顾白雾迷蒙,唯见弯弯的游道蜿蜓而行,两旁疏疏朗朗已然落叶的树则渐远渐模糊。犹犹豫豫地往前走,倒也似曾相识。路旁那棵光光的树,哦,春天里它曾满树绿叶,青春蓬勃。当年我走过它时,不是还满树白白的碎花么?是什么树呢?又是修路人告诉我们,是七星树。静心再看,但见它浑身或深或浅铁灰色,有些枝丫还挂了些小而圆的黑色果子!再往前走,便是陌生的景色,两旁已不见杂乱的芒草,惟留下一棵棵七星树,倒也错树有致。
行于浓雾里,行于褐红的木质游道之上,凉凉的风袭来,浓浓的水汽袭来。不时地停下来,看看那棵棵七星树,在淡淡的雾里,安静而又从容的模样。倘偶尔看到光光的枝丫间,躺着只小巧的鸟窝,便会高兴起来。但确乎没有鸟叫,茫茫天地间,好似只有我们几人,只有棵棵七星树,只有那只小黄狗。之前,一踏上游道,小黄狗跟在我们身后,浑身纯纯的黄色,干净的脸庞,好奇的眼神,自是令我们怜爱。我惊喜地唤它小黄,它时前时后时左时右,还不时停下脚步,惊奇地瞧瞧我们。走着走着,游道嘎然而止,该往哪走呢?我们疑惑了,小黄也抬头疑惑地看看我们。往左走,好似是往上走。试着走走,不对,便又返回来。往右走吧。
往上走,便是一条蜿蜒于厚厚芒草间的泥土小道,芒草已然枯黄,厚实的草丛里依然立着一棵棵七星树。到底走向哪里?我们且不管,一路上如梦如幻的情境,就令我们沉醉了。猛然间,一眼瞧见路旁那块木牌子,竟是祷泉湖的介绍文字,难道前方不远便到了?果然,再往前走,隐隐约约是坎坷不平的上山路,枯黄的芒草更密更深。似乎离祷泉湖不远了,但除了眼前的路清晰之外,一片茫然。抬头一瞧,一块大黑石屹立前方,之前没见过。难道已走过了?便立住脚,四处瞧瞧,湖到底在哪儿呢?依然茫然!看来,今天又与祷泉湖擦肩而过了。一时寂然,万般滋味涌上心头。
但我依然朝右张望,浓密的白雾,挡住了我热切的视线。浓郁的清新的水汽穿雾而来,绵绵而来,萦绕着我。于是,我清楚地知道,祷泉湖就安静地躺在近旁的浓雾里,昔日的芳草地已然枯黄,但汩汩的湖水仍缓缓地往前流淌,执着地朝着山下朝着山外奔。它穿过峡谷,走过浏阳大地,越来越丰沛,越来越从容,直至奔至湘江,至长江,至大海。
它激越的心,此时才安定下来,却陷入昏天昏地的思念。思念遥远的大围山,如此深沉,溢满蓝色的忧郁的泪水。
再遇多脉青冈
几番秋风吹过,大围山满山秋色,如一幅色泽浓郁的油画长卷。有的树树尖还带着些微的绿,渐变到树底则成了璀璨的黄,有的树便干脆一树金黄或一树火红,有的树则早已光光溜溜。于是,莽莽苍青之上,浮着团团明黄,暗红,鲜红,浅褐,及更多的灰色。块块灰色,或铁灰或浅灰,便是光光的树林。第二天是大晴天,浓雾已然消逝,阳光铺展在山山岭岭上,给油画涂抹上一层深深浅浅的明亮的光泽。安静的大围山忽而变得热闹起来:朴素的墨绿,沉寂的黄色,张扬的大红,富丽的金色,全都迎面而来。我们兴致勃勃地去爬船底窝。
长长的山谷形如船底,便是船底窝。窝底淌着一条曲折前行的溪流,穿行于岩壁磊石之间。毕竟是秋天,溪流水清见底,壁立处依然飞流直下,击水生花,玉珠四散。平缓处,水流从容,与石缠绵,水上浮着五彩的落叶。水声柔和、娇憨、清脆,透着一股童稚般的生气,时而笑语连连,时而调皮撩人。于是,远近高低,轻重缓急的山泉声汇成了大围山特有的奇妙乐曲。
从栗木桥出发,刚刚迈上游道,友人便欢呼,快点,快点,地上这么多尖栗!一看地上,果然躺着些褐色的树叶,大大小小已然裂开的尖栗球,间或几颗圆润的尖栗。上前抢着去捡,捡到一颗尖栗便好似捡到一颗欢欣,好似回到童年捡板栗的场景。其实,我还知道,大围山深处,还藏有很多很多弥猴桃,还有许多许多不知名的野果,现在也正是成熟时节。再看看躺在手心上那颗闪亮的尖栗,小巧玲珑,甚是可爱,便赶紧揣进口袋里。
走在游道上,其上零零碎碎地躺着些落叶,或绿或黄或红或褐色。一发现有尖栗,全都大呼小叫地去捡,或干脆拿起一枝小木棍,在落叶间拨弄来拨弄去。游道伴着溪流而行,我们不时坐在溪水边石头上,看远远近近的山色,倾听泉水哗哗声,琮琮声,静默声。水绕石而淌,大黑石大多光溜溜的,或立或卧,其上满布着大大的灰色斑点,还有团团青苔,间或片片落叶。丛丛兰草从石缝里钻出来,或依石而生。于是,流水,大石,兰草,还有水上的落叶,演绎为一幅清丽的画面,自山脚铺展而上。
爬山的人其实不多。走在密密的树林里,走在清澈透明的世界里,身心渐渐松懈,直至毫无纤尘。当然,看看那些高耸入云的树枝,再看看那些厚厚的枯黄的落叶,自然也知道森林并不像表面上安静平和。悄无声息间,大大小小的树会慢慢地行走,悄然地寻找合适自己的地方。在树群的缄默里,饱含着奇幻热烈的情绪、层层叠叠的秘密、密切无间的交往、无处不在的争斗,甚至存在着等级森严的顶级群落。只不过树的活动如此缓慢,以致人们可能要把一年当作一天来观察,才得以窥见它们生活的轨迹。
一路上山,那么多一棵棵或高或矮或大或小的树,自是令我眼花缭乱,所认识的树种最多不超过二十种。但我正朝一种树走,一种我多日来牵挂的树。走得累了,便抬头朝山顶的方向张望。我知道,就在高处某个山包上,有一群特别的树静静地在等着我。青冈,多脉青冈,水青冈。我走着,不时念叨着,友人们都被我撩拨起好奇心,脚步也零乱了起来。我的记忆其实有些模糊,只记得那个凉爽的夏天,正是万物蓬勃生长的时节。处处绿色,连喧哗的溪水也透着浅浅的绿。一开始只是天有些沉,湿润的空气特别新鲜纯净。我们心情大好,率性而行,走走停停,时而欣赏路边偶然冒出来的黑石上,时而呆在水声生动的溪流旁边,抑或干脆抬头看翠绿的树林。不知什么时候,竟淅淅沥沥下起了雨,自是都没有带伞,只得脱下外衣搭在头上。冷风嗖嗖而来,往回走已不可能,便埋头赶路。往上往上,却来到一个山坡,路旁都是密密麻麻的矮竹子。走没多久,路分岔了,有指路牌,左通往五指峰,右通往玉泉山庄。哦,我们长吁了一口气,很快就能走出重围了。
接下来,又是上坡路,来到一个山包上。竟然看到一棵奇特的树,众多树干亲密地围聚在一起,树冠如伞往四处张扬,浓密的嫩绿的树叶纯粹干净。我们站在树下惊叹着,哪来的如此奇特的水青冈树?那么多大小般配的树干怎么就长在一块呢?从一个树蔸长出来的么?在这千多米的高山怎么还能长得如此高大?再往前走,竟然还有不少棵,如家人般欢欣地团聚在一起,有水青冈,有多脉青冈,有单棵,更多的是众多树干依偎在一起,憨厚纯朴,婀娜娇媚。于是,不由再三流连,纷飞的雨也变得诗意盎然了。
而今,又到了山包上了。哪里还树冠如伞的水青冈树,只有一群光着枝丫的树,树下铺着枯黄的落叶。水青冈树竟然落叶,我始料未及,一时酸涩起来。便往前走几步,随地坐在几棵水青冈树跟前!阳光穿过光光的枝丫,灰色的树干上,那些或大或小的灰白色斑点,隐隐闪着光芒。主干始终直立向上,而光光的树枝,率性地旁逸斜出,其上生长的分枝越来越多,越来越细,偶尔还挂着一两片褐色的枯叶。其实,也挺好,至少看过它们青春勃发的模样。
站起来,恋恋地再往前走。行没多远,就在前方的小山包上,已然落叶的树丛里,竟然又有一群青翠的青冈树,我在找寻的多脉青冈树,自然都是众多树干围聚在一块呢!远远地,一棵棵看过去,多脉青冈树依然满树苍翠,一律灰白的树干,一律苍青色的树叶,浑身散发着成熟而又坚定的味道。我踩着厚厚的落叶,穿行于水青冈、多脉青冈树之间,任秋阳洒满全身,内心如此沉静从容,还有喜悦。千米之高山上,长有密密的树林,还有奇特的青冈树,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呀。一时间,广袤雄浑的大围山寂然无声,我高声呼喊起来,渴望它的回应。一时间,远远近近,落叶纷纷而下,如一场艳丽的花雨,沸沸扬扬。
就在那天,一路上不时地遇见几个背着蓝布袋的男人,我以为他们也是捡尖栗或者采山果的人。可一位瘦瘦的男人告诉我,他们在采种子,并从布袋里摸出一颗小落叶似的褐色种子。哦,摇钱树的种子。又是我从未见过。大围山到底藏有多少秘密?又有多少人能识得大围山真面目?
静默的围山书院
顺着船底窝走,离山顶不远,有一大块平地,有一片茂密的树林。游道旁满是尖栗树,我们便蹲下来找尖栗,捡到了一颗又一颗。猛一抬头,我惊愕地发现,竟然有石头彻的墙。石头墙不高,倒蛮长,前后左右都有。我站了起来,认真地看了看,毫无疑问,这里曾经有过人家。住在高高的山上,离群索居,那是什么滋味?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?
遥想昔日,环大围山麓都是荒蛮之地,渺无人烟。自明洪武年间后,才陆陆续续有客家人来此插草为标,自此扎根此地。比如白沙濠溪李氏始祖大犹公自河塘迁来此地,历经几百年发展,家业兴旺,就在狮口建起了李氏家庙。当我一眼看见飞檐翘角的李氏家庙,竟有说不出的欣喜。家庙出好,宗祠也好,都是昔日一个家族凝聚人心管理家族的地方,更是家族骄傲的象征。历经时代的变迁,李氏家庙还能如此完好地保留下来,依然散发着古朴的魅力,真是难得。
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思维,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,大多是历史前进的障碍,社会革命的对象。每一次改朝变代,便有一批旧贵族被击打得落花流水,从此风光不再,一批新贵族却蹁跹而来。少有名门望族,在浩瀚的历史能绵延下来。可至少在欧洲,古老的贵族比比皆是,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就让人吃惊。且不说其源远流长的历史,而是没有美第奇家族,就没有佛罗伦萨,就没有文艺复兴,那么世界的现代自是不可设想。其时,人的光辉照亮佛罗伦萨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子铺成的狭窄巷道,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,但这座城市却为近代欧洲奠定了基石。
放眼中国,从来就没有过如此门庭。即便在当朝一代,能幸运地延续下去。但当另一朝代取而代之,便灰飞烟灰。当然,儒家文化,作为一种大文化,已然艰难而又曲折地延续下来了,但那些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家族文化,大多受到严重的创伤。当在废墟上颤颤地站立起来,原气自是一时很难恢复,甚至从此崩溃离析。当然总是有人逆潮流而行,看到传统文化的灿烂之处,乃至在火热的革命年代勇敢地去维护去保存。当我行走于大围山麓,走过李氏家庙、鲁氏家庙、涂氏宗祠,乃至围山书院时,此种感触更为深刻。
环绕大围山,早期客家人,大多从福建、广东等省迁居而来。其客家山歌就如此唱道:“广东过来到浏阳,世人冒得俺格寒。早晨冒得鸡食米,夜脯冒得老鼠粮。”当年涂氏也从他乡来到茫茫大围山,且不说涂氏如何挣扎地立下了脚跟,其竟然嗅得了文化的芳香,绵延了耕读传家的传统。历经几代的发展,便传到涂启先一代。涂启先生于清道光十四年,自幼攻读,乃学富五车,后登癸酉科优贡。他却无意仕途,立意隐居梓里,潜心兴教,先后在浏阳城南书院、长沙岳麓书院等处任教。他还被地方推举为上东团总,鞠躬尽瘁地主编了《上东志》,传承上东几百年的历史文明。谭继洵慕名将爱子谭嗣同托付于他门下,学习儒家经史。授课时,涂不受前人注释束缚,自由发挥,常抒反对列强入侵的爱国感慨,给少年谭嗣同的思想极大的影响。
就在“戊戌变法”失败那年,已六十四岁的涂启先将自家的柑橘园捐献出来,并亲自主持建设事宜,建成了围山书院。书院刚刚建成,他却因劳累成疾,一病不起。念及创立书院的初衷,就有病重之时,他撰写了围山书院石柱联:心远自地偏,果能敬业乐群,此处亦名山广厦;民兴在经正,愿共守先待后,尽人为吾道干城。好在如他所愿,朗朗书声自此响彻在书院上空,大围山下人才蔚起。当此温暖的秋日,我站在书院跟前,静默之间,孩子的嬉闹声诵书声自远而来,由弱而强,如同弦律优美的乐曲。
试想,环大围山麓,散布其间星星点点的村落,那些勤勉的大围山人,世世代代未曾被重重大山阻隔了视线,他们渴求的目光总是热切地投向山外的世界。他们伐山开田,躬耕于田亩,求了温饱之后,便静下心来重拾儒家经典,思谋着治国齐家平天下之计。于是,众多有志之士,自这偏远之地,顺着浏阳河,走出重重大围山,乃至越走越远。但心依然向着大围山,累了倦了,故乡总是那抹最温情的印记。那么再振作起来,总得以新的姿态回到故乡吧。比如今日,东门古镇的浏河之畔,我就见到了一栋奇特的古院——廖家大屋,已有百多年的历史。那温暖的四合院,那精致的木雕,依然吟唱着琴棋书画的旋律。原本这栋廖家大屋,便是当地廖家后人早年出外打拼,远在浙江金华做纸生意,赚了钱便在当地建了这栋廖家大屋。百多年后,廖家后代竟能原封不动地将其大屋从金华搬迁至了大围山下。且不说其间花费的种种心思及金钱,那份回归故乡的情谊何其动人!
站在大屋跟前,倾听着小溪河水的潺潺之声,我真是感慨万千:大围山到底是怎样一座神奇的大山?
 大围山概况国家森林公园、国家地质公园
大围山概况国家森林公园、国家地质公园 旅游度假区浏阳大围山旅游度假区以山清水秀
旅游度假区浏阳大围山旅游度假区以山清水秀 景区景点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,总面积7万亩。分为:
景区景点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,总面积7万亩。分为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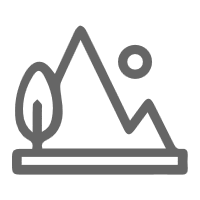 地质公园大围山第四纪冰川地质遗迹地貌明显
地质公园大围山第四纪冰川地质遗迹地貌明显 珍稀动植物大围山动植物资源丰富
珍稀动植物大围山动植物资源丰富
 0731-83488701
0731-83488701 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
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预定公众号(服务号)
预定公众号(服务号)
 出行小助手(订阅号)
出行小助手(订阅号)
